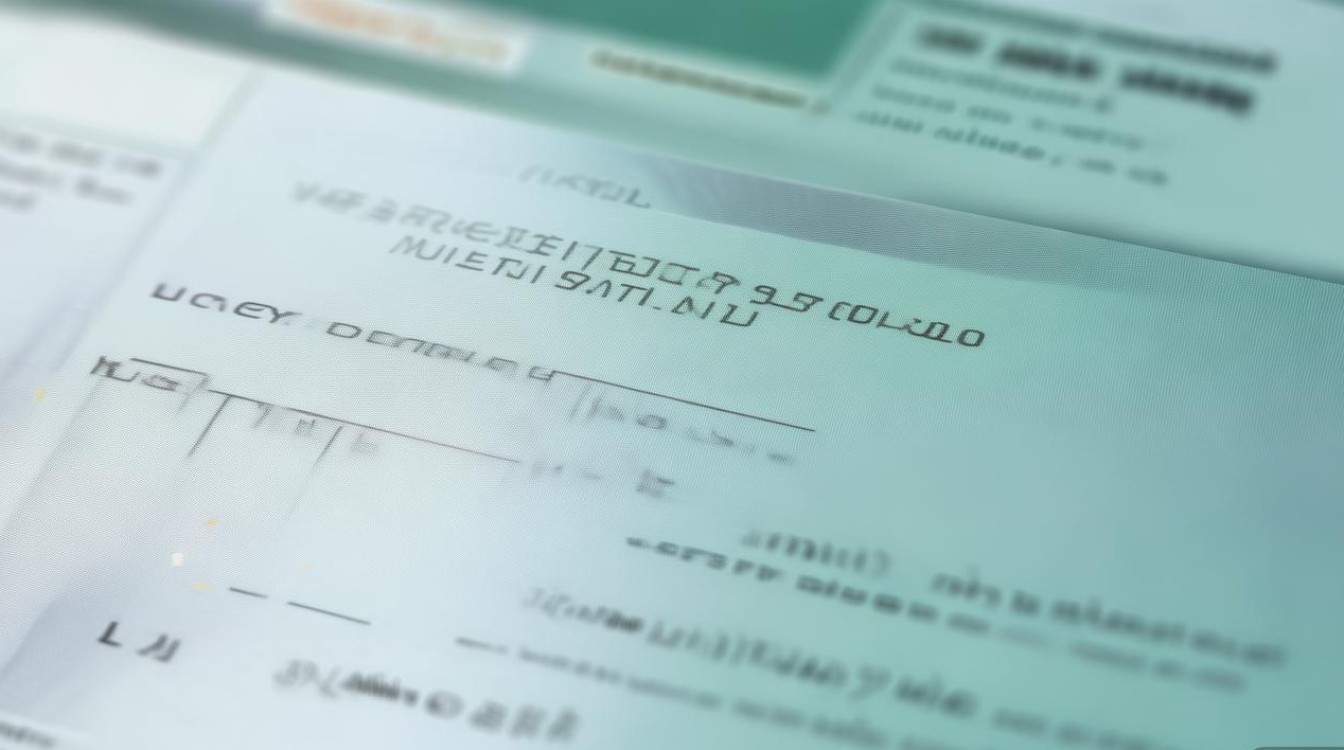作者 | 沈敏
近日,《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姊妹篇《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圆满收官。网友们发现,这部纯爱青春剧片头的“制片人”栏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非我思存。喜欢女性向言情小说的读者,一定被她的作品感动得落泪。这位以虐恋著称的知名网络作家,转型做纯爱剧制片人,地位再升级。
但事实上,随着近年来IP影视改编热潮的兴起,网络作家纷纷开辟新赛道,跨界影视领域,有的成为编剧,有的则承担起制片人、制作人、编剧等头衔。
在网络文学圈,有这样一句话:一流网络作家开公司,二流网络作家开工作室,三流网络作家是打字员。这句话简单直接,却不无道理。网络作家转型后交出的成绩单,勾勒出一幅作家转行做影视人的生态图景。
转型后作家的多重身份
网络作家的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编剧或剧本导演的身份参与小说影视改编的第一阶段——剧本创作。前者亲自操刀从故事梗概、人物传记到最终剧本完成的全过程。后者主要负责根据小说为编剧团队提供宏观影视意见。二是网络作家在幕后担任监制、制片人或制作人,统筹IP影视化运作。
1、网络作家转型做编剧:
宫廷剧鼻祖《后宫甄嬛传》及其续集《如懿传》均由原作者流潋紫执笔。前者创下豆瓣9分的收视纪录和高口碑,不仅多次在地面频道播出,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并输出海外。后者则实现了网络播放量和口碑的双丰收。而且两部小说改编成剧集后,豆瓣评分均高于原著口碑。可见影视改编赋予了IP第二次生命,深度挖掘了IP的多元价值。
荣获第30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的《琅琊榜》也邀请了原著作者海岩担任编剧,该剧不仅成为古装政论剧的标杆,斩获国内外多个电视剧奖项,还创造了电视剧口碑(豆瓣评分9.2)高于小说口碑(豆瓣评分8.5)的“奇观”。
以《杉杉来吃饭》《无声的别离》等甜蜜治愈言情小说闻名的网络作家顾漫,将文学领域对青春的感悟延伸至光影世界,曾参与电视剧版《无声的别离》的编剧和剧版《微微一笑很倾城》的编剧工作。两部风格迥异的甜虐剧集,斩获当年收视冠军和百亿流量,也在海外掀起国产青春剧旋风。
但并非所有转行写剧本的网络作家都是万无一失的。被誉为“网络历史小说第一人”的关岳,曾担任最近完结的古装悬疑剧《大宋北斗司》和去年开播的《夜帝》的编剧,但两部剧均不温不火。
除了大多数网络作家肩负起保护自己小说、担负起编剧重任外,也有一些“本末倒置”的“异类”,这些网络作家表现出极大的编剧热情,主动改编其他同行的小说。
明晓曦的《火焰之女》、唐家三少的《为了你我愿意爱全世界》、桐华的《步步惊心》、顾漫的《无声的别离》,这些家喻户晓的小说都被同一个人——墨宝非宝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近几年,她的编剧成绩单似乎比她的网络作家成绩单还要好。
2、网络写手转型做总监、制作人或者制作人:
有商业头脑的网文作家并不满足于仅仅收取影视改编的版权费,在与版权代理公司的合同到期之前,他们已经开始布局IP运营计划。成立公司、走资本化道路是他们的第一步。等到小说版权的授权合同到期,他们就会把版权拿回来,自己开发,自己公司把项目控制在自己手里,自己担任总监制、制片人或者制作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擅长商业运作的盗墓小说先驱之一南派三叔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2014年,南派三叔创办了南派梵语。他给自己贴上了“IP架构师”的标签,志在打造以刀比IP为核心,覆盖网剧、电影、漫画、游戏、广播剧、话剧等多个领域的泛娱乐王国。于是,从他的第三部影视作品《老九门》开始,几乎每一部以他小说为蓝本的影视作品的制片人名单里,都能看到南派梵语的身影。
南派三叔曾在亿元网剧《老九门》和热播作品《沙海》中担任总制片人和总编剧,近期杀青的超级网剧《重启之盗墓笔记》是南派番禺控股的首个影视项目,南派三叔担任总制片人和总编剧。
另一位具有灵活商业思维的女性网络作家是费我思存。她成为《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制片人并非偶然。因为该剧的制片人之一双杰影视公司,正是费我思存和著名出版人颜庆生于2015年共同创立的。这家定位为“中国言情梦工厂”的新影视公司将出品一部新作品,一部改编自费我思存最新小说《爱情如星》的女性职场励志剧。这也是她第二次担任制片人。
自我追求、她的经济、IP运营混乱
网络作家转型的三个原因
庞大的网络作家群体始于互联网崛起时代。相比其他行业,网络作家金字塔的分水岭更加明显。顶级白金网络作家年收入动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这还只是签约网络写作平台支付的费用。如果加上小说影视改编的版权费,收入更加可观,但这样的作家凤毛麟角,多数都是金字塔底层的普通作家,他们的收入和更新频率、点击率、读者反馈等数据挂钩,有的甚至和工薪阶层没什么区别。
因此,转型往往只发生在解决了温饱问题、拥有一定名气的网络作家身上。虽然跨界有风险,转型需谨慎,但有名利做后盾,这些网络作家也有底气挑战自己。无论他们转型后成为编剧、制片人、制作人还是总监,主要原因有三点。
首先,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四大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知名网络作家开始向最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迈进。比如总票房超50亿元的电影《战狼》《奋武耀基》《最后的捍卫者》的编剧,都是转型成功的佼佼者,他们原本擅长撰写军事题材的网络小说。前者出生于军人家庭,把从小灌输在身上的激情全部投入到文字中,在起点中文网拥有众多粉丝,因此对军事战争剧本了如指掌;后者甚至直言“写网文对我来说是乐趣,但能参与创作这样的军事重工业大片,我感到很荣幸。”
其次,女性受众审美趣味的变化,以及“她经济”的影响,也迫使部分女性网络作家顺应时代,改变轨迹。“得女人者得天下”的金科玉律,在网络文学和影视圈同样适用。据2018年底网络文学市场数据统计,在目前数字阅读的核心付费用户中,女性用户以56%的占比首次超过男性用户。这意味着网络小说的读者与影视剧的主流受众重合度较高,也说明女性网络作家的忠实读者转化为影视剧粉丝的概率很高。因此,女性作家在转型上有着天然的优势。
但随着新时代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表达欲望的加强,女性观众不再一头扎进痴情甜美或傻傻无脑的金手指剧里,她们更希望在小说或剧中看到独立自主、符合时代的女性形象。为满足女性观众的情感投射需求,一些女性作家开始抛弃霸道总裁爱上我的老套路,将创作触角辐射到多个类型。比如前文提到的“虐恋教母”飞我思存转身做甜美纯爱剧《好美的爱情》的制片人,墨宝飞宝担任古今中外多部爱情剧的编剧。
第三,IP爆炸导致乱象丛生,版权运营商的割韭菜让IP价值枯竭。身为原作者的网络作家心疼不已,决定自己出手,好好养育“孩子”。这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络作家、制作人主动请缨,自愿担任自己作品的编剧,比如合作《何以笙箫默》的顾漫和K-ton旗下的剧库,在项目开始之初就主动要求担任编剧。另一类是网络作家离开写作平台,自己开公司,运营小说IP的开发,以制作人的身份直接掌控项目,从产业链底层走到产业链前端,实现“逆袭”。
例如金合在成立星汉时光、江南成立玲珑文化,独立运营IP授权及影视开发;南派三叔成立南派泛娱乐,打造基于IP的泛娱乐王国;天蚕土豆成立微天传媒,运营开发自有作品;天下霸唱加入向上影业并担任COO等。
成功转型制作人的南派三叔曾说:“任何一个作家的作品被改编,他都必须是一个制作人,作家懂得制作是至关重要的。”
作家的蜕变能否为其作品赋予力量?
将二维的文字转化为三维的影像,是小说影视改编的难点,过去曾出现过不少因编剧与原作者不同而失败的案例。因此,当网络作家担任编剧时,书迷们往往松了一口气,制片方也感到安心。但作为不同的文学载体,小说与剧本出自同一个人之手,真的可以无缝转换吗?网络作家能否通过为自己的作品写剧本来赋能IP?客观来说,有利有弊。
首先,对于有编剧经验的网剧作家来说,他们了解剧本架构,因此在改编自己的小说时,可以尽可能忠实于人物设定、故事框架和世界观,从而更好地还原和保留原著的精髓,最大化地将书迷转化为剧迷,提前锁定一批基础受众,避免出现非作者当编剧,改编成非原著的影视作品,被书迷诟病的情况。例如:小说《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的作者海棠,大学时学的是编剧专业,所以她成为同名网剧的编剧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也可能存在立场冲突导致的困境,即:当原作者与编剧合作,在改编中需要做出选择时,他们会不忍心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下功夫,有时甚至不能以客观的角度去创作,影响剧本的呈现。
其次,缺乏编剧经验的网络作家与专业编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隔阂,并不是每个作家都适合转型做编剧。一般来说,编剧是2B创作,主要面向投资方、制片人、导演、演员等创作方,是一种为了满足他人而创作;网络作家是2C创作,写自己想写的故事,直接接受读者的反馈。相比较而言,编剧的工作属性比较被动,而网络作家的工作则更加主观。因此,当两者身份重叠在一起时,会有一个自我内化的磨合阶段,能否适应这个过程,是转型成功的关键。
编剧写剧本时,脑中想象画面,文字写下来,画面便诞生。而网络作家没有这种图文同步的意识,想法往往天马行空,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网络文章单看文字读起来很过瘾,但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却很难的原因。
在参与改编自小说《约定的日子》的同名电影编剧后,辛夷坞曾感叹:“电影剧本的语言就是镜头语言,哪怕是书中的同一段话,镜头语言是否合理可行,能不能和前后的其他镜头衔接起来,都是编剧需要考虑的,这与小说写作是两个专业的事情。”
为了确保原作者能为IP影视改编保驾护航,一些制片方通常会为其配备编剧团队配合工作。比如《花千骨》制片人唐丽君就专门为担任编剧的原作者Fresh果果召集了五六人的项目优化小组和一位资深编辑,用团队作战策略弥补网文作家转型的短板。
因此,一些有“自我意识”的网络作家始终呆在大本营,不敢越线。唐家三少明确表示,“不管怎样,我不会轻易转型,写作是我最重要的职业。”这位网络作家虽然不亲自改编剧本,但非常注重作品的IP运营,从实体书、漫画、游戏、影视、动画,到衍生品开发。唐家三少坚持不转型的原因,除了“对这个没兴趣”之外,还在于当编剧的收入不如主业的收入。
最后,如果网络作家转型升级成为制片人、制作人、监制等项目把关人,从宏观层面统筹剧本创作,也不一定能保证成功。因为从IP内容到发展策划,再到资本运作,不仅考验网络作家的整体商业思维和社交能力,更是对其综合素质的大考,没几个人能过关。
俗话说“无工具莫接”,但凡事都不是绝对的,只有通过反复试错,才能发现自己的潜力,知道自己的不足,找到适合自己的路。网络作家转型就像是作家跨界影视的一次实验,成功者为中国影视行业的进步贡献了一点力量,失败者也能为后人提供经验教训。我们应该乐观包容,但前提是转型跨界必须有纯粹的初衷或使命,而不是受利益驱动的投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