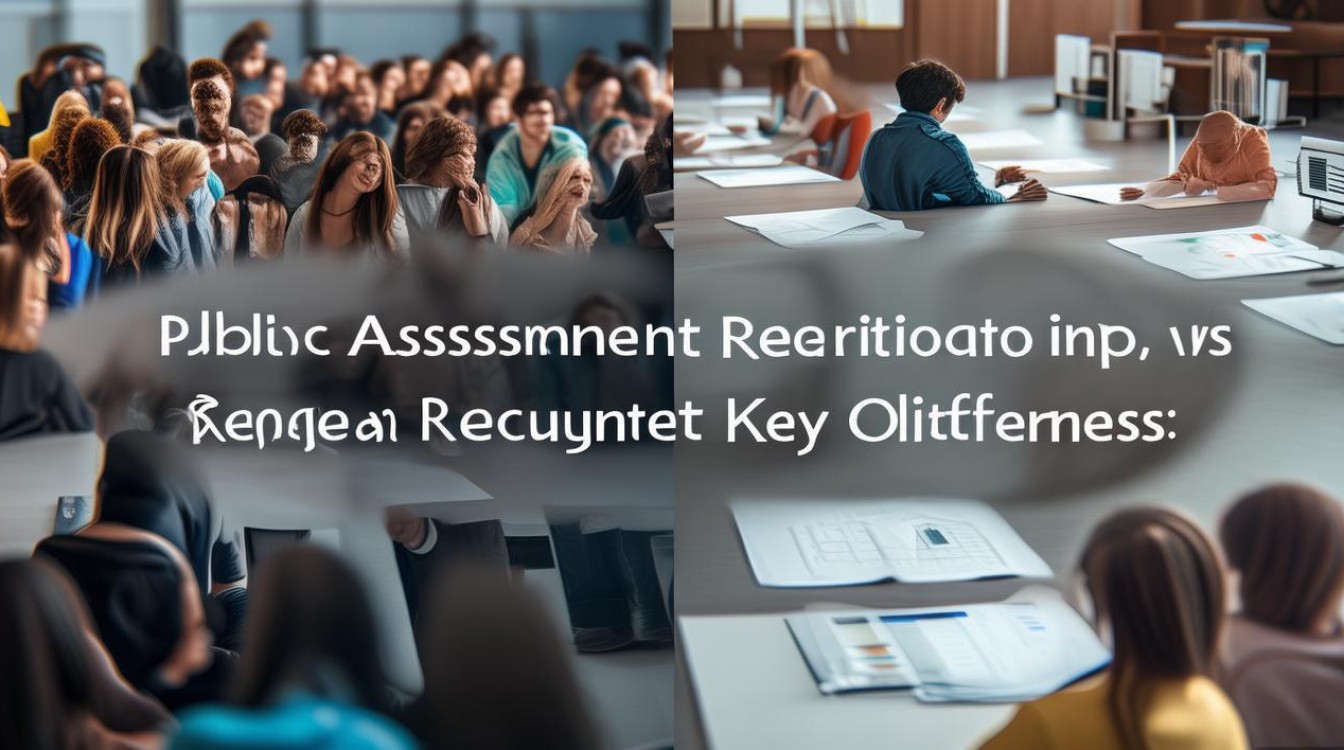2004 年,也就是 12 年前,在 CCTV 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活动中,马化腾向在座的嘉宾介绍了 QQ 的未来。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半开玩笑地对马化腾说,面对如此优质的客户,要发动猛烈的攻势,问他能否说服张瑞敏使用 QQ。
当时的马化腾还很青涩,像个生瓜蛋子,带着潮汕口音,意气风发地说:“QQ 是一种新的互联网沟通工具,能提高沟通的便捷性。互联网以后肯定会深入人们的生活,这种新的沟通方式会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然而,张瑞敏笑着婉拒道:“现在还没有说服我,谢谢你刚才精彩的介绍。”
今年腾讯成立 18 周年了。这些天,腾讯的市值不断飙升。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小片段流传开来,并且还演化出了一系列新版本。例如,马化腾向张瑞敏推销 QQ 却遭到拒绝,马化腾让张瑞敏收购 QQ 也被拒绝。
当年马化腾确实有过希望把 QQ 卖给新浪的想法。然而,经过一些好事者的拼凑组合,互联网野史便开始以讹传讹,并且越传越离谱,最后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有好事之人对这个原本是为丰富电视视觉的片段进行了一系列解读,这些解读像是“莫欺少年穷”那般。这与前几天马云面试肯德基被刷后终于报仇买下肯德基的故事有着相似之处,此片段成为了互联网上网友们用于刷微博、发微信,进行自我励志的小段子。
看完这一系列段子化和野史化的解读,确实让人挺感慨的。一方面,马化腾在当时 30 秒的时间里,确实没有说出很多新颖的观点。另一方面,对于企业家来说,确实没有太多精力去用于社交产品上的“无效社交”。
马化腾推销 QQ 遭拒的段子里,之前还有一系列被人们所忽视的铺垫。主持人向马化腾询问,QQ 主要是哪些人群在使用。马化腾的声音有些颤抖,用略带颤音的语调说道,主要是青少年特别喜爱,在 3.5 亿的用户当中,85%的人都是 30 岁以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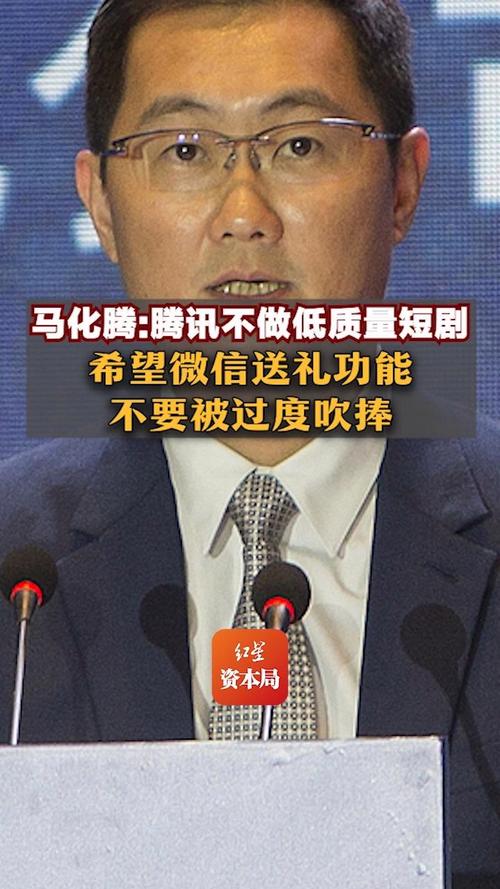
2004 年的 QQ 处于刚起步阶段。当时,QQ 主要被年轻人喜爱,其用途大多是唠嗑和网恋,与商务、办公几乎没有关系。大多数职场人士使用的是电子邮件和 MSN。2008 年是 MSN 的高峰期,其市场份额曾超过 60%。
QQ 真正开始快速发展并被职场人士广泛使用,至少是在 2010 年之后。那时大学老师在上课时曾说,用 QQ 的都是些小孩子,白领都使用 MSN。这与后期 QQ 增添的各种辅助办公功能有着紧密的联系。
所以说,让张瑞敏使用 QQ ,就如同在 2012 年让马云每天都上陌陌并与陌生人闲聊。这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企业家如张瑞敏每年需阅读 100 多本各类关于企业发展和战略规划的书籍,平均每 2 到 3 天就能读完一本,不存在耗费在 QQ 上的那种无效社交。所以 12 年前能看到马化腾向张瑞敏推荐 QQ 却遭拒绝,去年还能见到王健林对媒体讲,他基本上不使用微信,因为微信需要回复的内容太多,会耽误时间。
王健林称,他是通过漫长的会议来感知和了解互联网的。常常会有二三十人坐在一起进行讨论,具体次数都数不清了。做技术的人觉得可以,但做商务的人都觉得不靠谱,他认为这种方式肯定是不靠谱的。而做技术的人说出来后,做商业的一听就觉得这事有感觉。
当时这个说法在互联网上遭到了人们的嘲笑。不过这种笑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样一个笑话:有个乞丐说,要是当了皇帝,就下令村东边这条街上的粪全归自己,谁去拾就是犯法。还有一个乞丐瞪了他一眼,说要是自己当了皇帝,就有一个金斧子,天天用金斧子上山砍柴。
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认知世界依靠微信、微博、QQ。这是我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我们能有 965 的工作,闲暇时能在微信、微博上吐槽张瑞敏“不懂”互联网思维,能嘲笑王健林生了个不优秀的儿子,甚至还能调侃马云长得难看像个骗子。
但对于企业家来说,他们的时间极其宝贵,是在争分夺秒中度过的。每一分钟的时间,每一份精力都经过了精心的分配。企业家获取信息时是有选择性的。

这就如同《纸牌屋》中的那对总统夫妇,因为他们事务繁忙,每天的睡眠时间仅有 3 至 4 个小时,并且这三四个小时是间断的。倘若你嘲讽他们这种睡眠“不养生”,那笑话可就变得严重了。
你在吐槽张瑞敏“不懂”互联网思维时,他正在与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战略管理大师加里·哈默愉快交谈;你在嘲笑王健林生了个不争气的儿子时,他正在和高层领导人商议北京房价下个月的涨幅;你在调侃马云长得太难看时,他早已飞越重洋去美国与奥巴马共进午餐。
我们可以看到,张瑞敏不用 QQ,王健林不用微信。2013 年时,周鸿祎曾说:“我做不了教父级企业家,我不用微信!”马云说:“宁可死在来往的路上,也绝不活在微信的群里。”
这里面有企业家们保护自家产品的考虑,同时企业家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普通人完全不同。张瑞敏是变革者,王健林是变革者,马云是变革者,周鸿祎也是变革者。他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行为不能用我们普通人的目光去评价。用我们普通人的思维去看待企业家的生活,是很可笑的。
坦率而言,每当看到诸如马云一怒买下肯德基,马化腾推销 QQ 遭拒之类的“励志故事”或者“励志笑话”时,总会产生一丝丝的悲哀。
这种故事更像是屌丝的春药。屌丝们无法实现逆袭,只能在微博、微信上通过调侃他人来激励自己。然而,他们丝毫不知道马云、马化腾、张瑞敏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的思维方式和认知角度。就如同那两个乞丐幻想自己成为皇帝之后,到底是要用金斧子还是要去包场拾粪球一样。
这种笑话背后反映出了社会阶层的认知差异。真正可怕的并非财富差距,而是认知层面的阶梯式断崖。难怪最近流行的《北京折叠》这本魔幻现实主义科幻小说会引发如此大的轰动和震撼。
《北京折叠》中社会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人每天拥有 24 个小时,且这 24 个小时都用于制定社会规则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第三层次的穷人每天沉浸在网络垃圾信息里,会消耗掉自己仅有的 8 个小时。穷人们自始至终未被社会剥削,然而他们无法创造价值,也不能参与社会运作,所以只能统统被“折叠”到晚上,以尽量减少对社会的资源消耗。
没人想成为被折叠起来的那个群体。然而,如果仅仅依靠互联网的春药来进行自我激励,恐怕离被“折叠”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