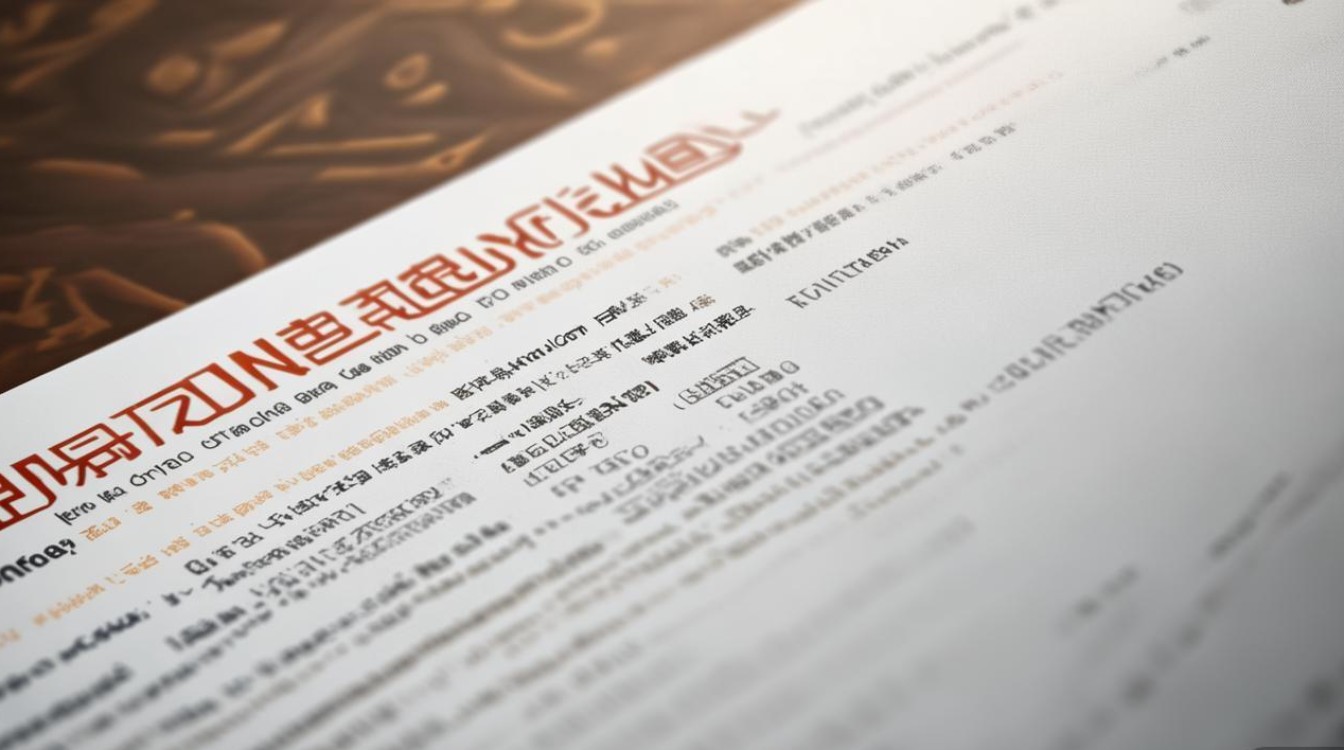本文以微电影《把乐带回家》为实例,论述了微电影通过制造情感认同来达成广告效果的重要性,以及广告产品怎样与情感相互阐释。总的来说,在植入广告泛滥的现今,微电影广告需要运用“去物质化”的方式来塑造广告效果。
【关键词】:微电影;植入广告;去物质化;情感认同;移情
商家可以通过情感创造出在现实中不存在的消费需求。例如在大雪天里喝百事可乐。当此时你对百事产生好感时,不得不承认,这并非是出于你自身需要消费它的意识,而是被商家成功植入了一种非自主意识的情感趋向。不过,这似乎正是植入广告应该达到的境界,这也是《把乐带回家》微电影广告系列所达到的一种境界。2014 年春节,百事可乐第三次推出了名为《把乐带回家》的年度贺岁微电影大片(以下简称《乐》《乐 2012》《乐 2013》《乐 2014》)。这部微电影赚足了好评、感动、泪水和欢乐。从 2012 年起,百事公司推出了第一部《乐 2012》。这部微电影获得了如潮赞美,于是百事可乐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出此类微电影,今年推出的是第三部。
一、微电影广告制造的情感认同
国人对电影植入广告并不陌生。我们或许不清楚史上第一个电影植入广告始于哪部电影,比如凯瑟琳·赫本主演的《非洲皇后号》。或许也没听说过大名鼎鼎的斯皮尔伯格在拍摄《ET》时推红了某个品牌的糖果[1-2]。但对于冯氏电影的植入广告,我们肯定是再熟悉不过的。《没完没了》中有中国银行;《手机》里有摩托罗拉;《天下无贼》中有惠普、宝马、中国移动;《非诚勿扰》中有奔驰、联想、海之蓝、春秋航空、保险公司、淘宝。在拍摄《非诚勿扰》电影期间,植入广告的金额高达 5000 万之多[3]。即便像《唐山大地震》这样严肃,甚至烙有民族伤痛的题材,冯导也能从容地将广告植入其中。冯小刚在广告植入电影这一商业操作手段上愈发驾轻就熟,与此同时,也遭遇了越来越多观众的诟病。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指出,植入性广告比单纯的广告更令人可憎,原因在于它剥夺了观众对于是否收看广告的选择权利。百事可乐推出了贺岁微电影系列《乐》。2012 年春节开始推出,每年都有。2014 年推出了第三部。每年的《乐》都能获得非常理想的网络点击率。调查显示,对该系列影片的认可和对百事植入产品的认可成正比[4]。这个结果证明了广告与剧情并非只有二元对立的呈现模式。
《乐》系列微电影广告的本质为广告。在该系列微电影广告中,观众得到了审美情结的满足。这是由于该系列微电影中的广告与情感相互交织,其效果得到了观众审美的认可。从这个角度看,微电影广告能让内心艺术的感受和情感的审美成为商业领域的消费元驱动力。这样,观众在观看微电影(其实是广告)时,不会为自己埋下的潜在消费而思考,却会感谢附加在商品上的艺术给心灵带来的慰藉。这也就使得本质是广告的微电影获得网络超高点击率变得顺理成章。
情感唱主戏,这更能满足碎片化时代的需求。在我们连走路都要低头搜索的时代,哪里有时间被大段大段推销的文字去消耗脑细胞呢?这时如果用一段动情的声画蒙太奇来替代,就如同以“艺术”的名义给脑细胞增添滋润,同时也为产品注入了情感的正能量。
二、与情感互文的产品植入
《乐》系列的社会背景存在共同之处。在泛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这个时代,浓浓的人情展现出了越来越大的离心力。《乐 2012》里,子女们为了事业、爱情和旅行,把老父亲(张国立饰)一个人留在家里过年;《乐 2013》中,大哥(南孚龙饰)和小弟(邓宁饰)为了多赚些钱,竟然趁别人处于危难之际高价出售食品,然而他们自己也是受危难的人群之一;《乐 2014》中,被乐叔(张国立饰)厚待的阿豪为了自己的利益,把乐叔的知遇之恩以及邻里多年相处的感情都抛到了脑后。在植入广告与情感互文这方面,《乐》的具体操作如下:励志情节被商品内化;邻里守望产生了消费移情;附会爱情进行了品牌演绎。
(一)励志情节的商品内化

在《乐 2013》里,小弟(邓宁饰)的改变是想证明,励志不只是理想的实现,做人的完善同样也是励志的演绎部分。在那被大学围困的废弃屋子中,小弟拿出了百事的薯片,在落难的同车人群里进行兜售。这一举动遭致了自己心仪的打工妹的鄙视和责问。自责的内心让小弟原本被利欲驱使的那个自我开始退缩。当司机老杨(张晨光饰)问到有没有人可以跑出这个雪山去求援时,小弟站了出来,尽管这个任务过程会关系到个人的安危。在《乐 2014》里,几年前有个没钱回家过年的落魄年轻人(由罗志祥饰演),他流浪在打烊的乐超市门口。乐叔(由张国立饰演)看到了这一幕,接着把一大袋年货交给了这个年轻人。一瓶百事可乐所蕴含的温情,开启了年轻人的信心。经过几年的奋斗,这名年轻人再次来到乐超市,凭借自己所学,将乐超市从危难中挽救了回来。在这两部片中,百事的产品充当了温情的推手,激励了两个年轻人的内心。乐叔说:“等你有能力想帮我的时候,你就去帮助那些需要你帮助的人,那时候你就会更快乐!”这句话就相当于直接用百事品牌来为励志年轻人代言。
微电影《父亲》中植入了雪佛兰品牌,而《乐》系列的微电影则内化了激人励志的浓浓温情。《父亲》中父女间、父子间的情感走向和戏剧张力更出色,不过它的雪佛兰车品牌植入显得有些生硬,与情节不太贴合。
(二)邻里守望的消费移情
《乐 2014》主要打的是邻里之间的情感牌,这种情感牌与百事产品所走的社区销售路线是高度相重合的。临危受命成为店长的年轻人表示“要有一颗助人为乐的心是最重要的”,还说“乐超市并非冰冷的商业机器,而是充满人情味的地方”。乐叔称“这个超市,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更是我们整个小区的,我们都是一家人”。在满眼皆是百事产品的乐超市中,这些话语无疑成为了百事产品对社区的宣言:街坊邻里才是百事的安身立命之根本。街坊邻居们纷纷表示“我们不会让乐超市关门的”“我老伴生前都是到这买东西的,要收购,问我老伴先”,面对黑心地产商。这段剧情是由邻里街坊推动的,乐超市就像百事仓库一样,通过它把简单如日常饮食的百事产品描绘成了与社区居民有着深厚感情的关系。在住宅商品化形成新型邻里关系的年代,剧中营造出了相互守望之情,这无疑给百事产品增添了正面形象分。在《乐 2013》里,一场大雪让原本互不相干的一车人变成了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他们只有面对面相互鼓励、背对背相互守望,才能找到求生之路,而维持他们在冰天雪地中撑下去的唯一能量就是几箱百事食品。这些食品起初是大哥和小弟手中趁机获取钱财的契机,后来却变成了大家相互守望、相互帮助的物质支撑和精神联系。百事从一个单纯的消费食品逐步完成了情感转移的过程,不再仅仅停留在只是商品的那种普通层面上。
(三)代言爱情的品牌演绎
爱情在百事系列微电影中也有着点睛的出彩效果。在《乐 2013》里,小弟给打工妹递了毛毯,这让后者心里萌生了心动的感觉;接着,小弟像趁火打劫一样高价售卖百事产品,使得打工妹刚刚萌生的爱意瞬间消逝;之后,小弟不顾自身安危,自告奋勇地去雪山营救大家,这又让打工妹陡然增加了担心;受伤的小弟给大家带来了救援,在担架上,小弟和打工妹心意相通,原本暗生的情绪变得明朗,最终成为了爱情。这个过程是《乐 2013》片中的一条叙事暗线。乐事薯片、百事可乐、果乐澄并非仅仅以广告植入的视觉符号的形式出现在该片中,而是成为了剧情的推动力量。打工妹在送给担架上的小弟的百事可乐上写下了“祝你”这两个字。“祝你百事可乐”这句话语,既融合了新年祝辞的内涵,又饱含着祝福俩人爱情甜蜜的意蕴。一罐饮料作为植入广告,在这里完全感觉不到有强塞进去的迹象。
在《乐 2014》中,爱情是不可忽视的情节元素。片中,爱情不是主导线索。年轻的女店员(杨幂饰)对电工(罗志祥饰),从最初的敌视,到质疑,到好奇,到钦佩,到仰视甚至崇拜,有着正常男女情感的观众,都会认为这是美好的一对。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没有理由不让他们未来牵手。乐超市这个地方即将关张,且里面充满了百事产品,这是他们共同面对的。员工阿豪出于私利出卖了集体。他们从相识到携手共进,是从电工来到乐超市想买百事可乐,却碰到了一筹莫展的女店员开始的。把产品演绎成爱情的代言物,成为了广告植入剧情的合理缘由。
三、去物质化的广告重构

在植入广告的操作过程中,商品似乎与剧情天然存在对立。一方面,编剧需要设计极具戏剧化的情节、冲突以及命运等;另一方面,却又因要植入广告元素而陷入反戏剧化的处境。剧情为了保持纯粹性会排斥商品,而商品为了突出自身功能又与剧情难以达成和谐,这就导致了广告植入微电影时面临困境。如此一来,商品与剧情就形成了具有先天差异的二元对立关系。近年来走红的女星杨幂执导了一部微电影,名为《交换旅行》。这部微电影存在植入广告,其植入的产品是“伊利每益添”牛奶。该片内容为杨幂饰演的职场白领,为释放工作压力,与身处巴黎的陌生人展开交换住处的异地旅行。该片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剧情空洞,二是植入的产品与空洞的剧情毫无关联。广告产品与男女演员的生硬搭配,换来的是网友的吐槽。在知名视频网站爱奇艺、酷 6 以及 PPS 网络电视等上,甚至播出了影评类的视频新闻,这些新闻“指责电影没有实际内容,毫无营养,看了是浪费时间,直呼上当受骗”[5]。《乐》系列微电影为这道难题提供了一个实践性的解决方案,即“去物质化”。这并非意味着广告产品这一物质化的形象不能在影片中出现,而是不能单纯为了让产品出现而让其出现,必须要符合剧情要求、情感走向以及推动情节的发展。2012 年春节到 2014 年春节这连续三年,《乐》系列微电影在网上为网民奉献了一道情感丰富的视听盛宴。不少跟帖都情动于衷,这是因为被剧情所感染。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年代,我们却要面对人情越来越冷漠、亲情越来越疏离、爱情越来越现实的情况。或许,《乐》系列找到了现实社会的痛处,为我们营造了一个能直击心灵的情感乌托邦。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确实俘虏了我们的情感。在片中,百事产品出现在情感和剧情需要之处。它可以作为超市货架背景,也可以作为情感信物传递,还可以作为高价兜售商品。它的出现助推了剧情发展,最后征服了我们的视听。
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再有物质的匮乏。物质不仅能够实现其“物质的消费”,还能够满足“身价的消费”“阶层的消费”“格调的消费”“情感的消费”等各类需求。在这样的情形下,物质对于人来说充满了各种主动性。而唯一不主动的,恰恰是物质的物质属性本身。例如,包包不只是用来放置物品的,饮料不只是用来解渴的,车不只是用来代步的,手表不只是用来显示时间的。在这种情形下,有必要充分强调产品的物质性吗?广告产品的“去物质化”,或许是每个微电影人在思考微电影剧本时都应当想到的。
四、结 语
我们身处现代化的年代。冰箱能凝固时间,电视机开拓了我们的空间,洗衣机让父母们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周末休憩。接着,电脑大幅增加了我们的工作能效,网络让我们能随意涉足人类的思想和世界的任何角落,移动互联使得我们在一低头和一抬头之间,就能够完成摇朋友、团购电影、下单淘宝等各种私人定制的事情。可是,从地理意义方面来看,现代化的过程伴生了更多个体从家庭、家族、集体中游离出去;从身份意义方面来看,现代化的过程也伴生了更多个体从民族中游离出去,这导致了各个层面传统集体的解体。传统结构所赋予的人情冷暖逐渐消散,人心之间开始变得疏离冷漠,并且越是肉体离散,就越需要精神的重聚与共享。
在笔者看来,《乐》系列提供了集体主义观照下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作为核心的百事产品,只是其中短暂出现的一部分,它不失时机且顺理成章地促使上述各种“情”重新聚集。这样,人们或是在啜泣中、或是在感叹中、或是在自省中完成了对一部微电影广告的欣赏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努力在产品的视觉符号方面通过增加出镜率的方式去引导观众购买,那属于比较低端的追求。而借助产品给观众植入一个情感的世界,才是真正的高端且有格调的。(袁小轩为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张树婷和吕艳丹所著的《有效的品牌传播》这本书,其出版地点是北京,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出版时间是 2008 年。
赵楠于 2012 年在成都理工大学完成了“微电影广告传播模式及效果研究”这一著作。